陳黃金菊
Languages:
中文
圖片:手民出版
編輯:劉文
大部分願意在台港譯介專業人文社科的譯者和出版社,都算是佛心。第一,跟《心靈雞湯》或《有錢人跟你想的不一樣》比起來,這類書的銷量不會太好。大多數人渴望物質層面的成功,但這些書通常都在跟讀者說,「成功」邏輯背後的瑕疵在哪;第二,因為銷量不佳,願意出版的出版社絕對不是抱持什麼樂觀的心情,而是他們覺得有某種必要、甚至是迫切的需求要讓更多人接觸到這些書;最重要的是,要去哪找合適的譯者?
要翻譯這類書籍的話,專業譯者的養成最為重要。「專業」並不是指,只有哲學系的人能譯介哲學作品,或只有文學系的人能翻譯文學作品,畢竟,學門之間的界線已不再這麼清楚了。例如,如果今天要翻譯沃林(Sheldon Wolin)的書,該找社會系、政治系還是哲學系出身的人?要翻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該找法文系還是哲學系的人?又或者,其實該找的是翻譯所的師生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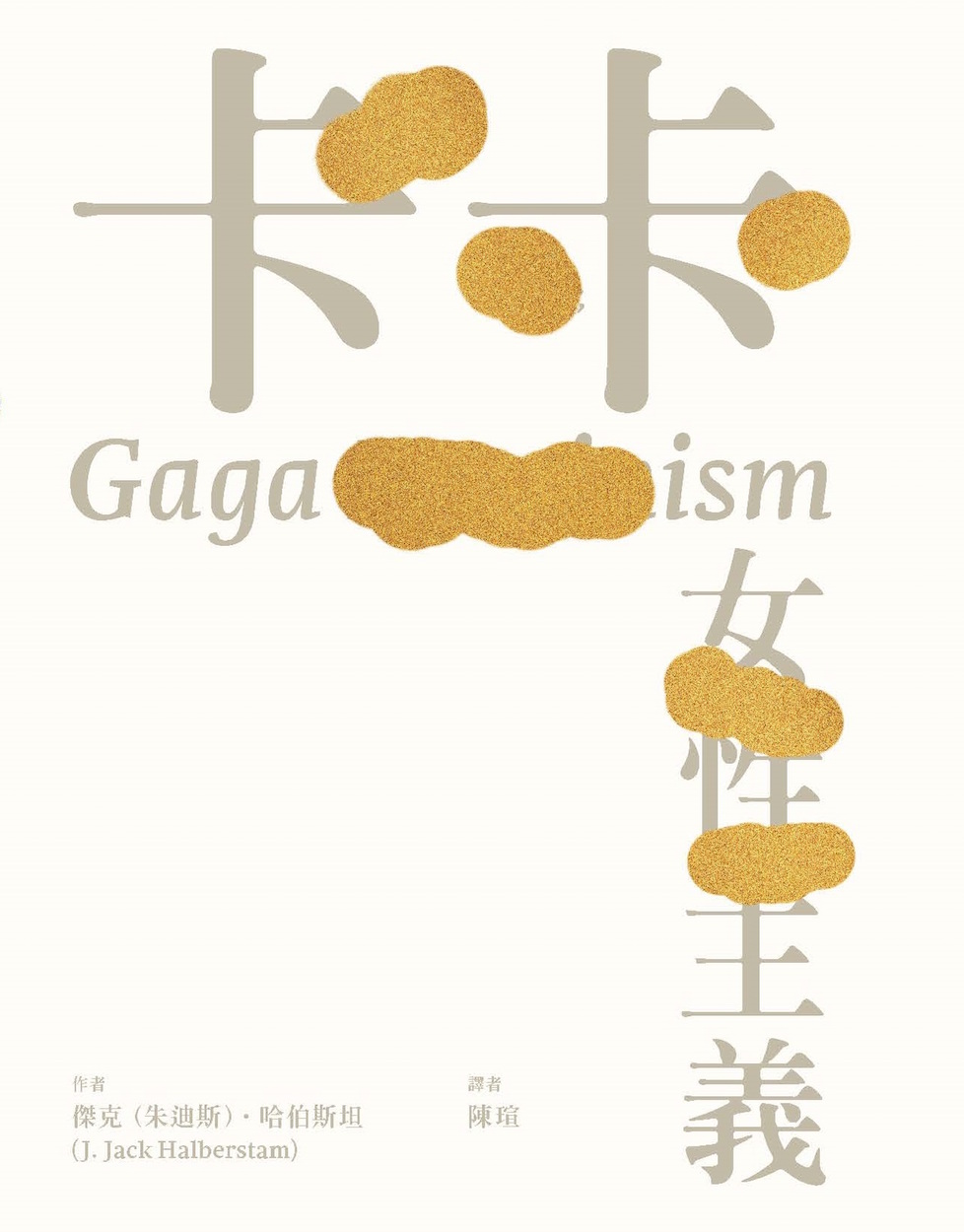 圖片:手民出版
圖片:手民出版
所謂的養成,主要是指譯者本身在翻譯與專業領域所下的功夫,與在學校修讀的科目不見得相關。首先,姑且不算語內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如把文言文譯成白話文),即使會講多個語言,也不代表就會翻譯。(應該許多人都體會過語句不順、錯誤百出的「雷書」吧。)除此之外,還有專業領域能力的養成。我想,鮮少會有人不承認,萬毓澤翻譯的《神經質主體》的的確確是個傑出的譯作,但萬毓澤既不是哲學系出身,也不是心理系出身,之所以能文筆流暢又有豐富的譯註,主因是因為譯者本身對當代歐陸哲學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手民去年(2019)出版的《卡卡女性主義》原文本身就相當精彩(可參考施舜翔為本書所寫的序),但在閱讀過程中,我實在忍不住佩服譯者陳瑄的功力——畢竟,市面上有許多內容精彩卻被翻譯毀掉的經典著作。凡是讀過作者哈伯斯坦(Jack J. Halberstam)著作的人,大概都被他那賤賤痞痞的幽默感所吸引。然而,語氣當屬翻譯一大難事。舉例來說,「You’re an idiot.」依照語境可以翻成「你是一個白痴。」(Google版本)、「你是白痴。」、「你這白痴。」、「你才白痴。」、「你才白痴咧!」、「你才是白痴呢!」等版本。一般來說,英文中缺少「呢」、「呀」等詞,因此,要翻譯語氣的話,就必須考驗譯者的閱讀和理解能力。
哈伯斯坦貫徹他幽默的風格,在《卡卡女性主義》中也創了幾個有趣的概念,其中之一為「鮟鱇陽性」。我讀完這部分時,除了一如往常笑了出來,更不禁佩服陳瑄翻譯語氣的功力。如下面這段:
Mumblecore films provide a justification for a new form of parasitical masculinity that I like to call “angler” masculinity, after the anglerfish. For those who have not read up on these crafty little creatures, male anglerfish are much smaller than the females; they can only survive by attaching to the larger female, fusing with her and mating with her. She then spawns eggs and baby fish … and her mate? He hangs on for dear life and feeds when she feeds. The mumblecore/angler male films by the Duplass brothers (Cyrus), Andrew Bujalski (Funny Ha Ha), but also inspired by Judd Apatow (Knocked Up) give this angler guy meaning—yes, he may be a loser, may lack a job, a purpose in life, ambition, charm, likeable qualities, this may all be true, but mumblecore imagines beautiful women throwing themselves at these men not despite their shortcomings but because of them. If there weren’t plenty of evidence in the real world for this phenomenon of smart women/slacker men couplings, mumblecore would be truly offensive.
在這段引文中,首先我們會注意到裡頭有一句長句(The mumblecore/angler male films […] because of them.)。雖然每位人文社科的譯者多少都對長句免疫了,但讀到長句時,心中大概還是免不了出現幾個髒字。畢竟,有時一個長句可以耗上譯者半個小時、一個下午,甚至更久。雖說英文句子結構能簡單理解為「主詞+動詞+受詞」,但翻譯過程中很少有「I hate you.」或「You disgust me.」的句子出現(老實說,這也不一定好翻)。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大量的連接詞跟子句串成一個句子,看起來簡單,但順譯逆譯都不是。這時候,就得考驗譯者的翻譯能力了。以下為陳瑄的譯文:
「呢喃核」替這種寄生蟲般的新陽剛氣質找到了理由——我稱之為「鮟鱇陽性」(”angler” masculinity),靈感來自鮟鱇魚(anglerfish)。要是你不熟悉鮟鱇魚的話,且讓我來說明。雄性鮟鱇魚的體型比雌性鮟鱇魚小,若要存活,就必須依附在體型較大的雌性鮟鱇魚身上,纏住她,與她交配。之後,雌性鮟鱇魚便會產卵,生出小鮟鱇魚⋯⋯至於她的伴侶呢?他繼續緊纏着她,她吃,他便跟着吃。因着杜普拉斯兄弟(Duplass brothers)的《重量級拖油瓶》、安德魯・布揚爾斯基(Andrew Bujalski)的《哈哈笑》和阿帕托的《好孕臨門》等「呢喃核」或「鮟鱇男」電影,「鮟鱇男」有了意義——是的,他可能是個魯蛇,他可能失業,人生意義、野心、魅力、討人喜歡的特質通通欠奉,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呢喃核」卻幻想美女們不會因此兒看不起他們,不但不會看不起,更會因為這些缺點而向他們投懷送抱。要是現實裡沒有太多這種「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的證據,「呢喃核」可真令人反感。
這裡的長句處理方式之一,是非常基本也非常必要的技巧:修習過翻譯的人都會知道,語句中常常隱含因果關係,但卻沒有「因為」、「所以」、「因此」等詞。這時候,如果譯文讀起來沒有原文的感覺時,可能就需要加上這些表明因果關係的詞。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把「smart women/slacker men couplings」翻成「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照字義上翻,這句話是「聰明女子/懶散男子的組合」,如果是我翻,可能會加一點點台語來翻出語氣,變成「聰明女子/荏懶(lám-nuā)男子組」;但陳瑄翻成「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倒是讓對比更為突出,也更能傳達出作者的諷刺語氣。
除此之外,譯者在性別研究與大眾文化研究領域的知識,除了能夠讓讀者能夠更貼近原文意涵,還能使這本書讀起來更通順。舉例來說,三十九頁有這麼一句:
無論是嫌男人不忠的「慾望師奶」,還是才剛離婚便感嘆同齡的單身漢買少見少的失婚女子(中略),甚至是會為難其他女人並逼迫她們自我懲罰的「女王蜂」(下略)。
翻到「女王蜂」時,譯者加了個譯註:「原文為”mean girls”,借用自電影《辣妹過招》(Mean Girls),羅薩林・威斯曼(Rosalind Wiseman)所寫的自助書《女王蜂與跟屁蟲》(Queen Bees and Wannabes)是構成該片的基礎。」
平時若沒有關注大眾文化,遇到「mean girls」的時候,可能只能翻出「卑鄙女子」之類的詞彙;就算有看過《辣妹過招》,也不見得會翻出「女王蜂」,因為譯者可能不知道《辣妹過招》奠基於《女王蜂與跟屁蟲》。研究過翻譯的人,想必知道翻譯必定會遺失一些物事,可能是語氣,可能是源頭語中的文化脈絡在目標語中完全缺席等。此時,若是譯者能適當為讀者添加脈絡,當可謂造福世人。(書中不乏此類的註釋。)
除此之外,陳瑄對當代文化研究和歐陸哲學也有一定的底子。例如,一直以來都對紀傑克(Slavoj Žižek,也就是《神經質主體》的原文作者)不甚滿意的哈伯斯坦,在《卡卡女性主義》中也再次對紀傑克提出批評,而翻譯這裡的困難之處,除了要能掌握(一樣講話賤賤的)紀傑克的想法之外,也要能理解當代文化研究的語言:
Zizek denounced the London riots in an article titled “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 making it seem as if the rioters were just mall-rats on a consumer rampage. When he addressed the OWS crowd, he commented: “Carnivals come cheap. What matters is the day after, when we will have to return to normal life. Will there be any changes then? I don’t want you to remember these days you know, like ‘oh, we were young, it was beautiful.’ Remember that our basic message is ‘We are allowed to think about alternatives.’” True indeed that the basic message is that there are always alternatives, but the idea that “carnivals come cheap” misses the point of the entire occupy movement. This is a carnival, and carnivals are precisely protests, and they are protests that never envision a return to “normal life” but see normal life as one of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and neocolonial power, a fiction used to bludgeon the unruly back into resignation.
陳瑄的譯文如下:
紀傑克在譴責倫敦暴動(London riots)的〈團結吧!世界的店舖竊賊〉(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一文中,把暴動者寫成是參與瘋狂購物的購物狂。而對於華爾街的佔領者,他則評論:「嘉年華會是廉價的。重要的是將來的日子,當我們回歸到正常生活的時候。那時候,會發生任何改變嗎?我可不希望你對這些日子的記憶會是『噢,我們可真年輕啊,那時候真是美好啊!』記住,我們的根本信息是『我們是被允許思考別的選擇的。』」沒錯,根本信息就是別的選擇一直存在,但說「嘉年華會是廉價的」卻是對整場佔領運動的誤讀。佔領運動正正就是嘉年華會,嘉年華會正正就是抗議,而抗議不但從未想像要回歸到「正常生活」,更視「正常生活」為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所虛構的假象,以假象逼迫不聽話者聽話。
書中出現的,還有如「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擬仿」(mimicry)、「情境主義」(situationism)等詞彙,雖然維基百科就能查到這些詞的意思,但要讓整個語句甚至文章讀起來通順,還是得對這些詞彙有基本的理解。
當然,這並不是個「完美」的譯本——真的有這種東西存在嗎?——本書有少少幾個完全不影響理解的錯字或排印錯誤(typos)。這裡也許能談談「完美譯本」這則迷思。在談論翻譯時,最常聽到的大概是無奈的「lost in translation」,也就是說,在翻譯中失去了某些物事,可能是語氣、脈絡等。對此,本身也為譯者的波利佐提(Mark Polizzotti)在二〇一八年出版了《同情叛徒:一則翻譯宣言》(Sympathy for the Traitor: A Translation Manifesto),他在書中指出,在閱讀譯本時,必定會有差異,但這些是「差異」,而不是譯本「失去」了什麼東西(difference rather than loss);同時,他也引用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œur)的話,表示我們最好「放棄『完美翻譯』的這種理想」。
近幾年,「哲普」一直是個備受討論的議題。哲普的本意應為將哲學(或曰思考)普及化,讓更多人接觸到「哲學」。以英語世界為例,讀了桑德爾的《正義》之後,有興趣的讀者能再去找許多經典的著作來閱讀;不過,在台灣(筆者對香港書市不甚瞭解),就以彌爾為例,除了《正義論》和《約翰.彌爾自傳》之外,幾乎找不太到彌爾其他的著作。或者,讀了《現象學十四講》,想深入理解現象學,但卻發現市面上現象學學者(如胡賽爾、海德格、梅洛龐蒂、沙特)的著作是少之又少。在缺乏專業(相對於所謂「大眾」)著作翻譯的情況下,「哲普」很容易變成「把哲學降低到讓普通人能懂的程度」,沒辦法讓「普通人」主動去接觸哲學。從這個角度來看,也許由專業譯者翻譯專業著作,反倒是一種更為澈底的「哲普」,能讓港台讀者直接閱讀到目前出版品中極為稀有的酷兒理論與性別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