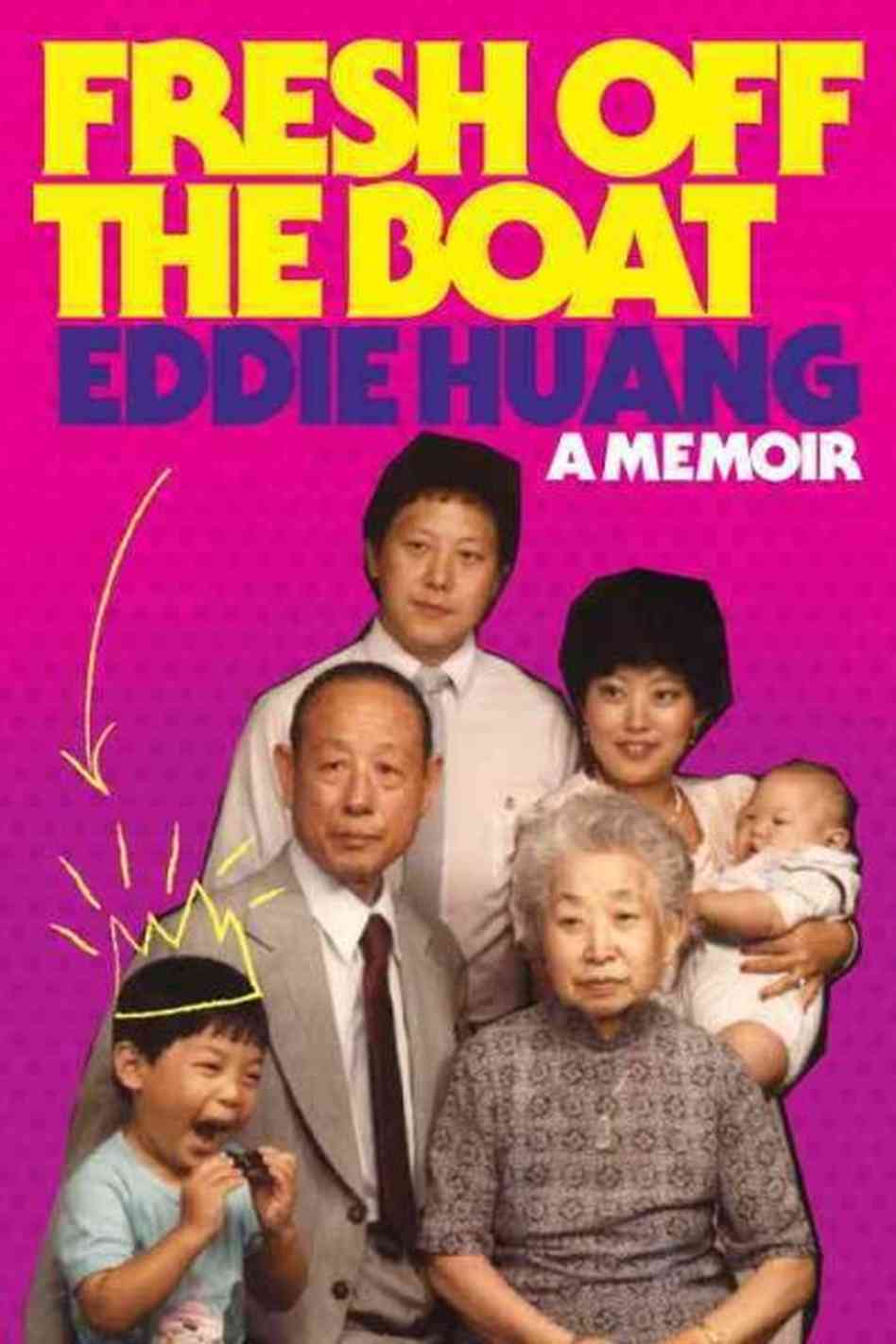丘琦欣
Languages:
中文 /// English
翻譯者:William Tsai
圖片:ABC
台裔美國人黃頤銘(Eddie Huang)自傳改編的《菜鳥新移民》電視劇,自二月初上映至今,不只受到亞裔美國人喜愛,主流美國電視觀眾也是一片好評。這部電視劇敘述了一個台裔美國人家庭搬到佛羅里達州的遭遇,紀錄了一個亞裔家庭適應美國社會規範的過程。
《菜鳥新移民》這部情境喜劇是以廚師兼媒體人黃頤銘的暢銷自傳為藍本改編的。黃頤銘是 Vice 頻道的美食節目「黃的世界」主持人,也是紐約市 BaoHaus 刈包餐廳的老闆,以及美國亞裔社會的意見領袖之一。黃頤銘在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也主演過獨角喜劇(stand-up comic),而後投入餐飲業,但他吸取了小時候父親經營牛排館的經驗。電視劇《菜鳥新移民》是對黃頤銘 2013 年發行的自傳進行的開放式改編,自傳書名同樣叫做《菜鳥新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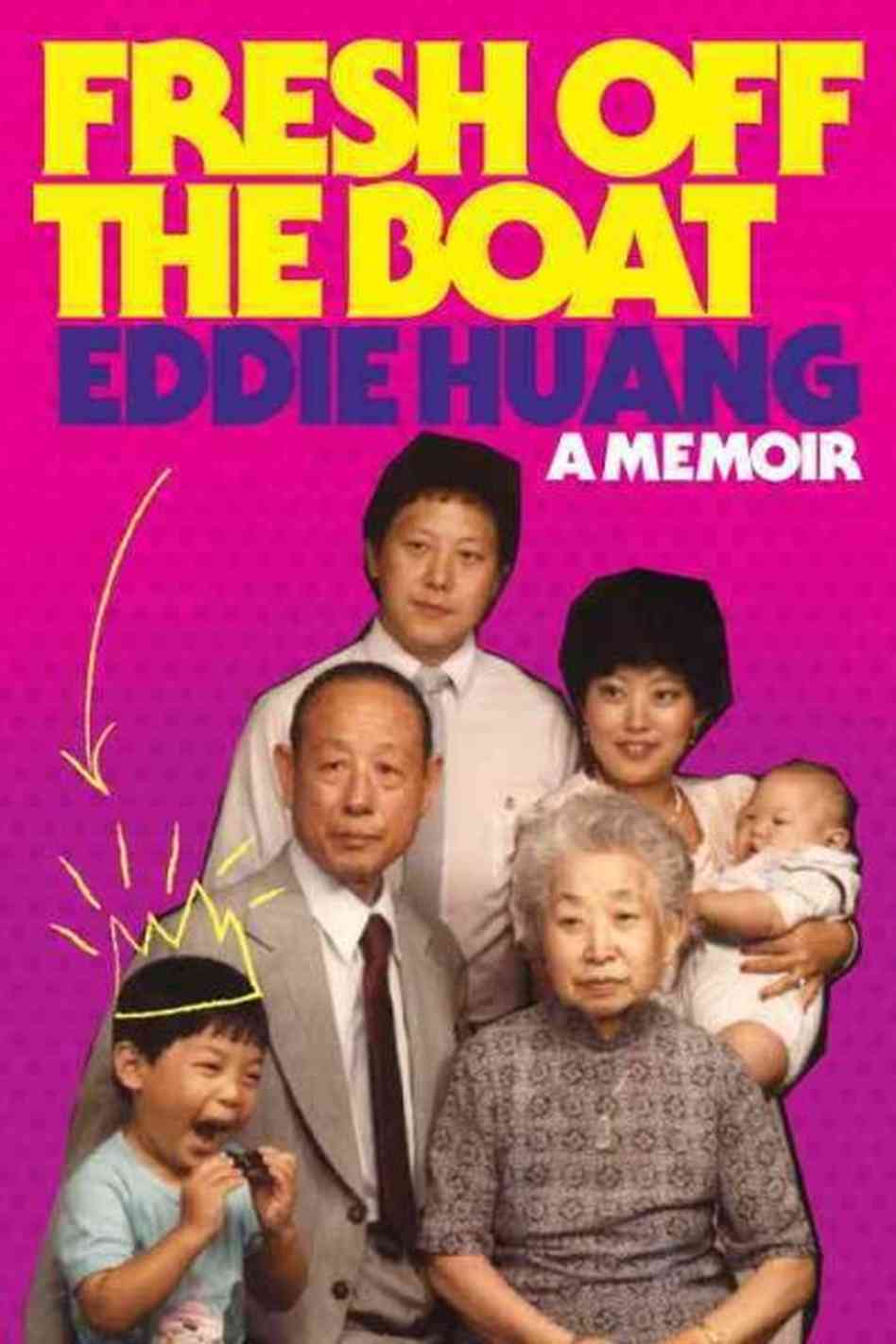 黃頤銘《菜鳥新移民》一書封面
黃頤銘《菜鳥新移民》一書封面
這部電視劇不只是亞裔美國人初次在美國主流電視頻道上獲得呈現,並且被稱許為亞裔美國人歷史性的勝利──他們為此已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在大眾媒體上爭取到亮相機會。就這點來說,經由該劇再現的所謂「亞裔美國人經驗」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亞裔美國人的聲援支持,也就毫不意外了。該劇能否維持人氣不衰仍有待觀察,但截至目前為止,該劇獲得了觀眾及評論家的一致肯定。 但在亞裔美國人明確地將《菜鳥新移民》的大受歡迎看作亞裔美國人在大眾媒體上獲得呈現的一大勝利之際,我們卻必須採取更為批判的立場。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的一部分興趣,來自於這樣的感受:我所生長的社群不會有另一個人撰文予以批判。我感覺到,亞裔美國人的主流意見往往盲目肯定《菜鳥新移民》,幾乎沒有人基於同等的顧慮而加以批判。
話說從頭,我的成長背景和黃頤銘幾乎完全相同。黃頤銘有時自稱是「台美人」,有時自稱「華裔美國人」,但也說過自己是「中台混血美國人」,他是外省人雙親的後代,也就是那些在 1949 年之後自中國逃難到台灣,占台灣總人口數 10%,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成為政治與經濟菁英,享有支配地位的一群人。
黃頤銘母親的家族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逃到台灣的,他的母親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家族中唯一出生在台灣的人。他母親一家在台灣創辦了一間獲利豐厚的紡織工廠,外祖父最後成了百萬富豪,而後移民美國再度白手起家。另一方面,他的父親出身追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員家庭,黃頤銘的祖父曾是內政部高級官員,對於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出力甚多;但這位祖父儘管仕途看好,卻似乎很早就脫離了國民黨,因為他反對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地人民的壓迫。黃頤銘的父親和母親一樣,都是在台灣出生。
我自己首先是半個台灣人,我父親來自客家裔的印尼華僑家庭,我猜想這讓我成了半個華人,儘管我父親認同印尼甚於台灣或中國,我在中國大陸也沒有親人。但我跟黃頤銘一樣都有個外省人祖父在國民黨政權做高官,我的外祖父當過台灣銀行的總經理。但我的外祖母是本省人,也就是占了台灣總人口數90%,國民黨政權到來之前已經在台灣住了幾百年的台灣在地人,她在台南長大,出生及接受教育都在日本統治時代。
說到我母親的家族,儘管一半本省、一半外省的背景體現在生長於台灣,卻能說一口京片子的華語也能說流利的台語這樣的弔詭上,我母親的家人仍然普遍自認為外省人,在政治上擁護國民黨。正因如此,我想我應該多少能夠理解黃頤銘互相衝突的認同感:我自認為是個台美人而不是華裔美國人,但我仍然參與許多華裔美國人的議題。
 黃頤銘在台北西門町「便所主題餐廳」用餐。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黃頤銘在台北西門町「便所主題餐廳」用餐。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於是,我的顧慮有一部分是關於台灣在電視劇中如何再現。當然,人們有時不免懷疑大多數美國人究竟有沒有聽過台灣,還是就直接把台灣和泰國混為一談了,連歐巴馬總統都犯過這種錯。既然《菜鳥新移民》是亞裔美國人在美國主流電視頻道中初次呈現,台灣在其中的任何樣貌,無疑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將會定型於美國人對台灣的認知中。要是台灣被呈現得像中國一樣,那些看過第一集的七百萬收視觀眾當然會讓其他更多的美國人也把台灣看成中國。而我懷疑,恐怕沒有其他的亞裔美國人,甚至台美人本身,也會抱持著這樣的顧慮觀賞這部電視劇。
但在另一方面,《菜鳥新移民》這樣的電視劇既是反思「亞裔美國人」內在緊張和矛盾的難得契機,它也同樣會是一個反身詰問全體亞裔美國人,以及他們與亞洲和美國關係的機會。關於亞裔美國人如何思考自我理解這件事,下文還會談到很多,這部電視劇正好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討論機會。
亞裔美國人革命有可能搬上螢光幕嗎?
評價《菜鳥新移民》這一文化現象時,人們立刻就會看到《菜鳥新移民》自傳書和《菜鳥新移民》電視劇之間的巨大落差。當然,電視劇並未自稱是改編黃頤銘的自傳,而是「靈感來自於」黃頤銘的書。
黃頤銘的自傳大部分是一個成長故事,他的家人隨著他逐漸長大、獨立自主而越來越無足輕重,但電視劇卻是在美國家庭喜劇常見的「永遠的童年」脈絡中演出他的故事。兩者更大的不同是,電視劇和黃頤銘自傳中坦白直率,偶爾自我剖白的敘述實在有段落差。就算電視劇試著引進一部分黃頤銘的嘻笑怒罵語調,第一順位的主導敘事仍舊是淨化過後的家庭喜劇。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宣傳照。站在圖中央的是扮演兒時黃頤銘的Hudson Yang。圖片:Bob D’Amico/ ABC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宣傳照。站在圖中央的是扮演兒時黃頤銘的Hudson Yang。圖片:Bob D’Amico/ ABC
或許這正是改編作品的危險之所在。但在整個《菜鳥新移民》現象中,這樣的差異則說明了讀出言外之意、剖析《菜鳥新移民》得以被主流美國白人接受的方式所在是必要的步驟,儘管在此同時,它也試圖進一步挑戰大眾媒體上再現可能性的邊界。於是,黃頤銘的自傳必須與電視劇分開來評價,也不能將黃頤銘直接看作電視劇中的自傳導演,他對電視劇的創意顯然沒有多大掌控空間。
說實話,就算大多數亞裔美國人都稱讚這部電視劇真實體現了他們的經驗,但《菜鳥新移民》很大一部分都在泛泛地操弄亞裔美國人性格的相關刻板印象。儘管演員表現優異,黃家的母親 Jessica Huang 作為全劇最突出的角色,實際上是跋扈專斷的亞裔「虎媽」刻板印象變體之一,她要求孩子們爭取難以達到的學業成績,並且介入管束孩子和丈夫的生活細節。黃頤銘的祖母和黃家同居,這個角色最引人注目之處正是在於幾乎成了龍套,家中其他人都說英語,只有她說華語,不然就像個被動的物體一樣坐在輪椅上被推著走──這是有歷史根據的,黃頤銘的祖母因為纏足而不能正常行走,儘管表達方式有些侮辱意味。黃頤銘父親 Louis Huang 的黑暗一面,則在電視劇角色的淨化之下被粉飾過去,事實上這位父親在台灣曾經混過幫派,有暴力傾向,是一位複雜而迷人的人物。黃頤銘青少年時代和家人的疏離也多半被抽離了真實的情緒或悲苦,去除掉這些則是為了製造出一個不具威脅性的產品,好讓美國電視觀眾吸收。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之所以如此成功,看來正是堅守了美國家庭喜劇的主導敘事套路有以致之。說實話,家庭喜劇作為一種美國機制似乎有些非比尋常之處,其中異性婚姻、一夫一妻的家庭是社會穩定的標誌。以家庭為主題的電視情境喜劇記錄了一家人的曲折起伏,但在每一集最後總要回復現狀,社會秩序重新得到確保。雖然家庭喜劇一開始都以白人家庭為取向,但隨著美國族群疆界的擴張,舉例來說,我們也開始能夠看到黑人家庭的情境喜劇,像是《天才老爹》(Cosby Show)、《新鮮王子妙事多》(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阿傑出少年》(Everybody Hates Chris)等等。現在,我們又有了亞裔美國人的家庭喜劇,這顯然標示著美國族群疆界如今已經夠寬大,能夠容納亞裔美國人了。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中無疑對黃頤銘的複雜性進行了簡化。在我想來,亞裔美國人要是有考量到黃頤銘的其他作品,以及《菜鳥新移民》一書作為成長敘事的本質,在《菜鳥新移民》改編成家庭喜劇之後就應該立刻提高警覺。可是亞裔美國人太渴望接受《菜鳥新移民》是一部再現他們生活經驗的電視劇了,甚至到了讓人懷疑這部電視劇的成功是否多少取決於戲外的其他因素。不免讓人覺得,只要這部電視劇能夠刻劃出亞裔美國人經驗的某些面向,又不至於用過分冒犯的方式輕蔑亞裔人士,亞裔美國人無論如何都會加以吹捧。很有可能,黃頤銘自己建立在挑戰「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之上的公眾形象,也多少讓這部看上去足以打破陳腐刻板印象的電視劇得以傳播到亞裔美國人圈子之外。
儘管這部電視劇從 Hudson Yang 飾演的黃頤銘,到吳恬敏(Constance Wu)飾演的 Jessica Huang,完全不乏演員的精彩表演,但《菜鳥新移民》上演至今的敘事卻始終是千篇一律的移民家庭努力融入美國,最後以再次肯定「美國民族大熔爐」敘事而畫下句點,而非指出民族同化論的局限。這部電視劇到目前為止對亞裔美國人所表達的,則是它從亞裔美國人的經驗中吸收了夠多特徵,使得千篇一律的民族大熔爐敘事相較於其他同化敘事多了個異樣的賣點。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宣傳照。圖片:ABC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宣傳照。圖片:ABC
也許這本身就指出了「亞裔美國人認同」這一自我想像的某些局限。亞裔美國人的這一切奮鬥真的是為了維護自身不同於美國白人的經驗之獨特性,或者只不過是另一個「歸化美國人」族群,到頭來只是指望著獲得美國接納?我們恐怕得問問自己,為什麼就是會有用這種形式改編黃頤銘自傳的意識型態需求,還有黃頤銘的自傳怎麼能被改編成這樣?
我們必須把黃頤銘的自傳《菜鳥新移民》一書和電視劇《菜鳥新移民》區分開來,各自評價。我們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把兩者簡化為一,好像它們只不過是同一現象的兩種分支。但我們因此得先探討《菜鳥新移民》這本書,它不只是電視劇的原始材料而已,既然黃頤銘的公眾形象多半是以這本書為基礎,它或許也是電視劇的基本邏輯之所在。
追尋文化本真性
黃頤銘的自傳相當好讀。敘事的流動偶爾有些不順,但多半只是小毛病。黃頤銘也會在其中一些片段突然離題,為了敘事流暢起見,恐怕需要再做刪節。產生問題的多半是對話部分。由於撰寫自傳是一門選擇性回憶的藝術,人們從自己雜亂無章的記憶裡編輯出一個能夠卒讀的故事,對話就必須直指重點,同時聽來又得像是自然而然的交談。但黃頤銘有些時候太容易在對話裡說教。他的角色所說的話,有時聽來實在不太像日常的談話。
總的來說,《菜鳥新移民》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也不令人意外,既然它的確寫得精彩又引人入勝。黃頤銘的才華尤其充分表現在描繪個人經驗,並將自己的經驗和讀者連結起來這一點上。黃頤銘的自傳能夠傳達亞裔美國人的聲音,並與他們的經驗產生共鳴,部分原因也在於他的個人經驗十分廣泛。的確,除了融入新學校、面對白人小孩的種族歧視辱罵等等日常生活的鬥爭之外,黃頤銘還會聯想到其他高度相關卻不常被提及的經驗,這是值得肯定的。立刻想到的或許正是那些道出我個人經驗的片段,包括不得不和那些讓人受不了的白人僑民打交道,他們想盡辦法要證明自己比你這個亞裔美國人更懂亞洲,好讓他們待在亞洲的時間能產生某種真實性。或者是與其他不同的第二代亞洲人經驗相遇,比方說,遇見那些和亞裔美國人有所不同的亞裔歐洲人,更別提亞裔美國人自身經驗之中的種種不同組合。
但我們可以從這本書裡清楚看到,黃頤銘是如何運用他從黑人嘻哈文化得來的靈感,在大眾媒體上建構出一個以顛覆「模範亞裔少數」刻板印象為中心的自我再現。比方說,他在 2012 年《觀察家報》的一篇人物專訪裡提到自己從小到大是怎麼被說成「Chigger」,即「中國黑鬼」,因為他喜愛嘻哈和饒舌歌,還有身為亞裔而形同賤民的地位,儘管黃頤銘談這些事的時候其實流露出自豪。
在更大程度上,黃頤銘還試圖表現出一種看似基進的公眾形象,他自稱受到 Malcolm X 和其他揭露美國種族與階級不正義的著名黑人運動者啟發。正因如此,黃頤銘也在書中的其他部分痛斥其他亞裔美國人甚至亞洲人不夠反叛,太想擁抱「模範少數」刻板印象或源自集體權威的亞洲社會規範,這些也都是他的反傳統形象所要對抗的。不管怎麼說,黃頤銘也很強調「本真性」這個概念,既是身為努力保存菜餚原有風味的台菜、中國菜主廚,也在於他對亞裔背景的自覺意識。黃頤銘似乎既想要保存一部分來自先人的觀念,同時卻又想對抗它們。
正如他在《菜鳥新移民》一書中宣稱自己與「在美國出生的華人」(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這種型態格格不入,因為他的叛逆言論「在這些人看來永遠不夠『亞裔』」(頁158)。接下來的對話是這樣進行:
「孩子,你就做你自己啊,你這個亞洲瘋子!你對食物甚麼都懂,語言說得很溜,又去過台灣,你比所有這些傢伙都更像華人。」 「對啊,但這跟 ABC 們想要的不一樣。我爸爸不是工程師也不是醫生,他有一把自動手槍,以前我看卡通的時候他就把它放在我頭上。」 「這有任何關係嗎?」 「關係可大了,老兄,你聽過那些人開會時講些什麼嗎?他們都巴不得在竹編天花板(bamboo ceiling,指美國職場對亞裔的抑制和差別待遇,一如壓抑女性的「玻璃天花板」)下過活,全都吃模範少數神話這一套;我受不了這種狗屁。他們根本不明白,我們在中國、台灣或者菲律賓想做甚麼就能做什麼。在美國,我們只許扮演一種角色:會算術的太監!你看過《致命羅密歐》(Romeo Must Die)嗎?李連杰根本沒人鳥(gets NO PUSSY)!」(頁158)
說真的,這段對話充分說明了黃頤銘的大男人主義,我們稍後還會再多談一些。但黃頤銘宣稱在亞洲「我們想做什麼就做甚麼」的同時,他也在其他段落裡痛批亞洲人,理由則詭異地與他批判美國人對亞裔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如同他在 BaoHaus 開幕之後遇到的一個場景:
「我們遇到最大的挑戰來自於那些小氣又沒品的台灣人。我記得有個女孩子跑來跟我說:『你知道嗎,這些刈包比台灣賣得還貴。台北賣的刈包更大,而且價錢不到一美元!』 『那麼,你何不花九百美元買張機票,回去買個一塊錢的刈包?』」(頁267)
你對美國不滿意?回中國去啊,噢,我是說,回台灣去,你這中國佬!接著,黃頤銘試圖用一種笨拙的方式,把這個經驗和他對亞洲人同化於美國社會主流的憤怒連結起來。他繼續寫道:
「我在 BaoHaus 工作時又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好像又回到了中國學校,和那些心胸狹小又保守,SAT 測驗教材上沒寫就連個屁都不懂的亞洲人相處的時候。」(頁267)
人們實在看不太出來便宜的刈包和亞裔在文化上的某種奴性之間有何關聯。這段話反倒說出了黃頤銘的亞裔認同歸根究柢是矛盾的。
我們或許可以在黃頤銘的本真性追尋當中找到些自打嘴巴的成份。例如:亞裔美國人及美國的其他少數族裔三不五時都會強烈批判「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有時還不經意流露出對文化混合(cultural hybridization)的敵視,以及某種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不過人們卻又不免意外,即使亞裔美國人宣揚著從亞洲繼承而來的文化,但他們往往缺乏對亞洲的具體知識。黃頤銘清楚看見了這樣的矛盾,他在自傳中談到,個人對於文化祖國的語言流利程度及知識多寡,有時竟成了亞裔美國人之間互相比較以證明自己更具文化本真性的標準,這段敘述證明了他對亞裔美國人追尋認同的種種自相矛盾、彼此牴觸方式有著高度自覺。
黃頤銘敏銳地察覺到追求文化本真性的競逐,可是正如先前的引文所述,黃頤銘習慣把好幾個議題混為一談,他宣稱亞裔美國人缺少對亞洲的具體認識,同時又不認為自己懂更多;但他其實還是對自己高度的文化知識和流利語言能力感到自豪。事實上,黃頤銘在其中一章自稱要超越一切邊界,卻又往往強調各種邊界。有時他甚至也成了自己所批判的對象。話說回來,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或離散認同(diasporic identity)有時只不過是國族認同的放大版,人們因此得以自稱比那些認同單一國族的人更為優越,因為他們比起自限於狹隘文化邊界,無法真正「跨越邊界」的人擁有更多更廣大的邊界。 儘管黃頤銘偶爾表示美國人在某些方面虧欠了亞裔,他自己卻還是會毫無理由地以美國人的姿態敵視亞裔。
黃皮膚,黑面具
我們還要進一步批判黃頤銘自己採用的基進形象,而這是關於他建立形象時所展現的厭女心態,還有他自稱基進叛逆背後的基進時尚本質。如同法農(Frantz Fanon)首先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闡述的,殖民地經驗的其中一部分是將殖民征服看作是對男性國族主義自我的創傷,因此,男性被殖民者是透過男性殖民者對女性被殖民者的性支配體驗到殖民支配,於是,他渴望支配殖民統治者的(白種)女人,以補償他受到的閹割。
 黃頤銘在台灣墾丁。圖片:黃的世界 / Vice 媒體
黃頤銘在台灣墾丁。圖片:黃的世界 / Vice 媒體
法農的精神分析方法當然適用於亞裔第二代在美國的經驗,並且同樣適用於黃頤銘努力仿效的美國黑人經驗。可以這麼說,黑人男性炫耀珠光寶氣,與包括白種女人在內的不同女性雜交的幫派饒舌(gangsta rap)形象,正是對富裕美國白人的怪誕惡搞及反叛,白人的社會名望遮掩了他們對有色人種女性的階級支配及性暴力這一黑暗面。以荒誕扭曲的型態呈現美國白人的特徵,逐漸被看作是一種賦權(empowering)行動,不管怎麼說,對於男性確實如此;但也同時證明了法農的洞見,被殖民者透過重現並扭曲殖民權力的譬喻而展現能動性。
黃頤銘採用脫胎於嘻哈文化的形象,以及自傳中好幾處談論亞洲動作明星「沒人鳥」(“never get pussy”)的說法也正是如此。同理,他也提到了一些跟人打架、或是被警察傳喚的事件,有可能是為了炫耀他的大男人侵略性。黃頤銘看待女人的態度也成了貫穿全書的主題之一,如同他在 Vice 頻道「黃的世界」節目中一再使用「shawty」這個詞(順帶一提,城市辭典對這個詞的定義是「性感辣妹」,給和我一樣不熟悉這個詞的人參考),還有他一天到晚對鏡頭下女性的魅力品頭論足。
回到法農的理論,在黃頤銘自傳裡特別生動的內容,是「粉紅奶頭」那一章。那一章敘述的是黃頤銘對於和粉紅色乳頭的女人(白種女人)作愛充滿好奇心,那是和棕色乳頭的女性(亞裔女人)不一樣的女人,最後他如願和這種女性上床。人們忍不住懷疑黃頤銘對自己的心態究竟有多少自覺;他的自傳裡有一段對女性主義的簡短說明,但這段內容和全書的其他內容卻顯得格格不入。
至於黃頤銘運用的基進論述,則似乎是他整個表演性基進主義傾向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想當 Malcolm X,有時候看起來還真的像。亞裔族群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與黑人基進主義攜手合作的歷史,如今已被毫不批判地肯定為少數族群共同奮鬥,喚起當今美國社會重視種族不正義問題的典範,而這正是當代文化研究及亞裔研究的矛盾之所在。黃頤銘談到大學生活,提起他在文化研究課堂上的見聞時,他似乎也成了這種現象的產物。
 或許是一個佛洛伊德式倒錯(無意間的潛意識流露),同樣來自《菜鳥新移民》第三集「友情 vs. 金錢」。圖片:ABC
或許是一個佛洛伊德式倒錯(無意間的潛意識流露),同樣來自《菜鳥新移民》第三集「友情 vs. 金錢」。圖片:ABC
人們有時不免疑惑,就算是在文化研究領域裡,美國境內少數族群的交流經驗好像也不免還是被放在一個巨大、統一的架構下探討。美國少數族裔的經驗在文化研究中被簡化成好像每個族裔都共享同一套經驗,因此自然而然會聯手結盟;但是沒有人關注和討論少數族群彼此之間的來回拉鋸,以及這樣的交流未必能在政治上導向進步之路。
亞裔與黑人的關係實際上正是一個族群看待另一族群的文化刻板印象交互強化,直到兩敗俱傷的歷程。說真的,倘若在美國對抗種族刻板印象的結果,竟是讓文化迷思中因為陽具太小而被閹割的亞裔男人試圖模仿黑人,好重振他們的男性雄風──因為黑人往往被美國社會投注了過多的性慾意象,被定性在黑人大雕的文化迷思裡──那麼實在不能說有太大助益。
文化覆蓋物
或許正因如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何正是黃頤銘的自傳能夠以電視劇《菜鳥新移民》的形式成為美國文化工業的有機護根層。或許正是黃頤銘的反傳統企圖從一開始就太容易被美國白人的文化風尚給收割──事實上,它對某些大有問題的文化譬喻進行的批判不但不夠基進,還恰恰體現著它們;於是,《菜鳥新移民》一書也就無法抗拒美國文化機器的收編企圖。畢竟,同化過程中必定有所掙扎,但終究是大勢所趨。黃頤銘或許抵抗著亞裔同化這套敘事,但我們還無法得知這種掙扎本身是否其實是同化過程的一部份。
 以下這個廣告是由美國廣播公司(ABC)經由《菜鳥新移民》的官方推特帳號發表的。後來黃頤銘公開批判這個廣告複製種族刻板印象。圖片:ABC
以下這個廣告是由美國廣播公司(ABC)經由《菜鳥新移民》的官方推特帳號發表的。後來黃頤銘公開批判這個廣告複製種族刻板印象。圖片:ABC
而那些最熱情推崇《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恐怕正是渴望同化的亞裔美國人,無論他們自己承不承認。黃頤銘自我標榜的基進主義,使這部電視劇相較於其他同化敘事顯得更反叛一些,但這正足以讓亞裔美國人說服自己放下惱人的反思,不再擔心自己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向同化讓步。
應當肯定的是,黃頤銘對於電視劇呈現的有限性是有強烈自覺的。因此他才會在《菜鳥新移民》上映之前,在《兀鷹》(Vulture)雜誌發表文章,批評這部電視劇和它呈現他自傳的方式,為這部片引發的討論加碼。類似的狀況還有:他在 Vice 頻道主持的「黃的世界」美食節目中,有時會為了突破限制而做出驚人之舉。在莫斯科拍攝的那一集裡,黃頤銘請到的來賓是一位住在莫斯科,因拍攝俄國生活經驗的影片而在網路上爆紅的美國黑人,但黃頤銘隨後卻強烈抨擊這位黑人為了出名而操弄「黑人在俄國」的種族刻板印象。就在同一集裡,黃頤銘隨後還請來一位吉爾吉斯的移民工,好讓他表現出俄國成功與富強之外的另一面。
雖然《菜鳥新移民》電視劇不是黃頤銘可以充分掌控創意的文化產品,但原先的自傳內容還是有些面向沿用到了電視劇中。比方說,《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第三集的一部分情節是少年時期的黃頤銘為了炫耀和受人歡迎而渴望跟一個白種女人上床。人們看了不免懷疑,電視劇有時似乎想盡辦法要拋開原著的拘束,主觀上是這樣期望,但人們也看得出來,電視劇在這方面的失敗,正說明了原著提供的原始材料本身很容易被消化。這或許也是同樣決定於戲劇之外的社會因素。因此,我們還要繼續探討黃頤銘全部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再現問題。
追尋文化本真性?還是追尋美國?
黃頤銘對於他主持的「黃的世界」節目,在創意上的掌控空間比《菜鳥新移民》電視劇更大,這讓「黃的世界」節目更為細密而複雜;但我們仍能從他對亞洲的再現中,指出一些足以削弱他自稱要追求的「文化本真性」之問題所在。的確,正如上文所說的,黃頤銘有時會出人意表地挑戰大眾再現的限度,他在莫斯科的那集節目尤其如此。但在其他時候,黃頤銘自己在將外國場景奇特化(exoticizing),好讓美國觀眾消費這點上則是難辭其咎。
 黃頤銘在中國成都。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黃頤銘在中國成都。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儘管黃頤銘和偶然遇見的人們通常是友善地互動,尤其他似乎總被在地的孩子吸引而跑去和他們玩耍,但他在各國的不同地點來往移動時,表現出來的卻還是典型美國人的模樣,色彩鮮豔的衣服和高分貝的說話聲立刻就暴露了他是外地人。
黃頤銘不像其他許多美食節目主持人那樣,從來不會自稱熟知某地的「內行人門道」,比方說,他在每個不同地方總是明確地向觀眾介紹那些帶著他品嘗美食的在地嚮導。
大多數時候,黃頤銘都盡力對在地風俗表示尊重,或是不著痕跡地以文化習俗來說明在地菜餚的複雜難解之處,而不是輕率地貶低不同飲食習慣──儘管有些時候,黃頤銘就是沒辦法吃下某些在地菜餚。可是人們又不免產生這種惱人的疑惑:黃頤銘到不同地方追尋在地特色時,他所尋找的其實是美國在外國各地留下的印記,作為調節外表看來不可調和的文化差異。因此他才會在台灣或蒙古報導重金屬樂隊,或是在上海報導一家美國人開的中國菜餐廳。
黃頤銘比起其他同類型節目主持人更為出色之處,在於他嘗試聚焦於所到之處的社會議題。比如說,他在中國時就把握機會對中國的國家防火牆(Great Firewall)發表了一段長篇大論,也對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還有危害牧民生計的蒙古採礦計畫進行深度報導。
可是再一次,黃頤銘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批評他所見的亞洲文化集體心態,另一方面,他又隱隱然為了美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促成了個人表達空間的開放而欣喜,或者應該說,是美國脈絡下的個人表達空間。除此之外,黃頤銘也發現自己處在一個試圖批判美國對這些國家造成經濟發展不均的立場,可即使他確實認知到,並如實呈現出自己正在討論的是一種需要多方面考量的現象,他仍不免陷入兩難。
邊界之間
於是當我們回過頭來繼續提出這些問題,並且評價黃頤銘對台灣和中國的採訪時,令我驚愕的是,他介紹台灣的兩集節目,很明顯比介紹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更缺乏尊重。這很有可能是因為黃頤銘對台灣的瞭解相較於對其他國家更多,他在台灣的這兩集中完全不需要在地嚮導,且或許是更能放得開而去取笑他所熟悉的這些事物。事實上,雖然黃頤銘在介紹中國的那幾集裡確實運用了他的湖南祖籍,以及依據祖先出生地作為認同對象的中國文化傳統,自我介紹為美籍華人,但他對中國現今明確可見的政治、文化及經濟矛盾並不怎麼挖苦嘲弄。反觀他在台灣就更傾向於自我介紹為台美人,或是中台混血美國人。
可是一般而言,黃頤銘對台灣更缺乏尊重,對於台灣各地的檳榔西施、士林夜市的大屌燒,或是台灣師範大學校園裡的扮裝表演等各種現象,可想而知全都引來了大男人沙文式的評價(幸好,黃頤銘還沒深入台南探訪廟會或葬禮上的電子花車舞孃)。黃頤銘也很頻繁地和台灣在地人接觸,但有時卻嘲笑那些聽不懂自己說甚麼的老年人。
 黃頤銘和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林昶佐)及團員共進晚餐。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黃頤銘和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林昶佐)及團員共進晚餐。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為了聚焦於台灣的社會議題,黃頤銘訪問了重金屬創作樂手、著名的台獨運動者,也是閃靈樂團主唱和時代力量黨(New Power Party)創辦人林昶佐(Freddy Lim)。黃頤銘看待台灣獨立議題實際上是公正而平衡的,他試著聚焦在自己的台灣工作人員和林昶佐的不同看法,由此揭示台灣人對於台灣獨立議題的立場差異,但由於黃頤銘的工作人員英文程度不如林昶佐而未能完全奏效。儘管黃頤銘似乎對林昶佐有些批評,但他能夠立刻抓住台灣獨立政治的歷史盲點,指出台灣要想擺脫中國的侵吞,就只能在美國霸權下尋求保護,這樣的敏銳度還是應當肯定。這個事實是許多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都沒能想清楚的。
可是黃頤銘同時也在取笑林昶佐,取笑林昶佐聽不出他唱的重金屬歌曲歌詞,林昶佐自己在閃靈的英文歌詞中用了「腐肉」(carrion)這個詞卻不懂什麼意思,也取笑林昶佐家裡的可愛風裝潢和他的重金屬形象多麼不搭調,並且特意凸顯林昶佐偶爾不確定該怎麼回應自己時的講話不輪轉。黃頤銘用更認真的語氣談論中國社會議題時,人們多少感受到他對台灣延續至今的民主弊病其實不甚了解,多半把台灣看做一個過去社會爭議已多半得到解決的國家,也沒有仔細考慮台灣所遭遇的中國威脅。於是,儘管他嘗試運用自己對社會議題的普遍意識描述台灣的社會議題,但似乎又不很認真看待這些議題──這倒不是說他不關心,但他覺得台灣的問題多半都已經解決了。
當然,這和大多數台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時候,黃頤銘表達的政治觀點似乎又來自於他的外省人家庭背景,比如他說,雖然共產黨統治和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但這些文化卻在台灣和海外華人社群保存了下來,因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傳統文化得以回歸中國,不過如今傳統文化的保存又遭受資本主義發展掛帥的威脅。毫無疑問,這正是國民黨努力要說服台灣人民,以確保台灣和中國文化密不可分這一信念的一套說詞。也正如上文所言,這樣的說法同時是典型美國人的思維,黃頤銘不經意地指出了經濟自由市場確立帶來的文化自由化,卻也批判自由市場導致的經濟發展不均。
但這種觀點同時也證明了,黃頤銘看待美國之外的脈絡是很簡化的,把自己奠基於美國的立場,投射到亞洲脈絡上:黃頤銘到處提倡保存亞洲真正的傳統文化,不讓亞洲傳統受到美國文化的侵奪,他特別強調保存亞洲傳統,不讓傳統文化在上世紀共產革命的偏差行徑之後,又受到自由市場的威脅。因此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要努力保存固有的傳統。當然問題絕不那麼簡單:中國人今日對抗資本主義時,用以抵制自由市場破壞性影響的資源,正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這同樣也是一種對抗當今資本主義的堅守「傳統」,但這個傳統和黃頤銘所珍重的卻是大相逕庭。不用說,歷史這筆糊塗帳絕不是一個來自遠方的人這麼輕易就能解決的。
華人?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順著以上的思路推演,人們也就發現了:關於台灣,黃頤銘的「中台混血美國人」認同是受制於美國人對中國和台灣不加區別的認知,這使得黃頤銘對中國產生認同感。沒錯,黃頤銘的祖父母都來自中國大陸,他自己也是外省家庭出身,但他的父母都是在台灣出生的,因此黃頤銘講的華語帶點台灣腔;儘管這可能是我從類似經驗想像的,但我發現黃頤銘回應說話方式和台灣華語相當不同的中國大陸人的時候,似乎會慢半拍。他的自傳和介紹台灣的兩集節目也證明了,包括返鄉探親在內的兒時記憶似乎也是和台灣有關,而不是中國。
黃頤銘混雜的認同感算不上什麼大問題,畢竟他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可以自由選擇要做哪一國人,要是他生長在台灣,自稱為「中國人」可能會產生比較大的問題。認同中國大陸的外省家庭確實是傾向於自稱「中國人」更甚於「台灣人」的,但這兩個詞可以隨時交替使用。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宣傳照。圖片:ABC
《菜鳥新移民》電視劇宣傳照。圖片:ABC
「文化中國」這個存在於某些領域的想法,在那些與祖國逐漸斷了聯絡的海外華人之中傳承了好幾代,要是黃頤銘接受這個想法,很有可能是他的外省家庭背景和家庭教養所致。不過,這也有可能是一條受美國社會影響而成的途徑。畢竟,美國人作為「民族大熔爐」的公民,是基於遠祖的血統來定義一個人是哪一國的後裔,例如,一個人就算家族在美國生活了好幾代,和義大利再也沒有聯繫,他還是能夠以義大利的文化和歷史來產生豐富的文化認同感而做個「義大利人」。
可是儘管這一切過往的歷史距離黃頤銘已經如此遙遠,人們卻發現黃頤銘祖先的歷史已經以一種雜亂無章的方式,成為他引以自豪的對象。黃頤銘似乎對於外祖母的湖南人血統感到驕傲,因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湖南人是毛澤東,以及「左宗棠雞」命名來源的左宗棠;但就這個例子來說,他對毛澤東帶來巨大災害的政策,以及美國的中國菜館扭曲中國菜原味的怪異歷史都抱持批判態度。他在其他時候似乎也對自己的祖父當過國民黨高官,母親來自台灣的有錢人家感到自豪,儘管他到底熟不熟悉這段過去實在令人疑惑。不過既然台灣歷史與文化在美國少為人知,能提供他更多資源產生文化認同感的也就是中國歷史了。
以後應該能夠看得更清楚,《菜鳥新移民》電視劇至今為止都不太區分台灣和中國。但是台美人普遍讚許《菜鳥新移民》的一切,原因是這部電視劇使他們有了得到再現的感受,如此而已。因此,我必須指出黃頤銘的認同感中存在著矛盾,當作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實例教學。
儘管我以為中國人對《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反應,可能會把《菜鳥新移民》視為《北京人在紐約》──以中國移民在美國生活為題材的中國電視連續劇──的倒轉版本。我卻也發現,中國不太需要捍衛自己的文化再現形象,因為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在我看來,考慮《菜鳥新移民》現象如何再現台灣是更為重要的,因為全世界缺乏對台灣的認知;但反觀那些知道這部電視劇的台灣人,卻也往往給予讚揚,理由則近似於台美人或亞裔美國人。
黃頤銘抗拒循規蹈矩的社會規範或許沒有錯,但他同時也被標舉為足以在美國呈現台灣的英雄人物。既然台灣人有時還是死守著亞洲社會循規蹈矩的幽靈,與美國這個崇尚個人特色的烏托邦形成對立,黃頤銘甚至就只因為這些緣故,因為他被人們認知的美式個人主義而受到推崇。台灣人到目前為止對黃頤銘還沒有甚麼要求,無論是好是壞,他都會成為台灣人形象的再現。但台灣人理當有所要求的。
為何需要批判?
《菜鳥新移民》的演員和劇組,尤其是女主角吳恬敏在《菜鳥新移民》上一篇相當有力的專訪,試圖以一部電視劇不可能再現亞裔美國人的全部經驗這一論點化解批評;同樣的,劇組人員也提到了《菜鳥新移民》一劇的歷史性地位,即使有著許多問題,這部電視劇仍因它的歷史意義而有其重要性。
無庸置疑,第一點很大程度上是事實。不可能用一部作品再現所有人。正因如此,我在這篇文章裡幾乎都不是以「無法像我一樣再現亞裔美國人的經驗」為由批判黃頤銘和《菜鳥新移民》,也無意以我個人的「中台混血美國人」經驗挑戰他的經驗──即使我就是要喚起黃頤銘和《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注意,他們對於再現台灣必須更加用心,因為這將對台灣意義重大。
 黃頤銘和Philochko。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黃頤銘和Philochko。圖片:「黃的世界」/ Vice 媒體
如果因為《菜鳥新移民》電視劇的歷史地位就批評不得,這種說法就非常有問題了。正如「史上第一部」這個說法能帶來極其強大的力量,同樣的,「歷史」作為一種理論依據,也能透過「少數族裔必須等待最終獲得歷史救贖的時刻到來」一說拒絕少數族裔享有平等權利,而這正是一種讓批評噤聲的手段。
當一個人經由黃頤銘這樣的方式受到大眾矚目,他真的能夠免於招致批評嗎?黃頤銘在《菜鳥新移民》一書中道出了自己對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景仰,因為歐巴馬是第一任黑人總統,為美國少數族裔首開先例。就這點而言,「歐巴馬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都是我的老鄉。」(頁224)可是話說回來,就算他有這樣的地位,又是現任美國總統,難道我們也不該批評他嗎?就我所知,一旦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就沒有禁區可言了;坦白說,我這話也是對自己說的。
黃頤銘自己對於單一個人成為整個群體代表所產生的問題其實再清楚不過。一如他在「黃的世界」莫斯科那一集中,對製作網路影片賣弄「黑人在俄國」刻板印象而躍升媒體名人的布魯克林黑人 Philochko,基於「恣意將刻板印象………….和污名,輸出到一個缺乏相關脈絡,不知如何應對的外國」的理由加以批判時所說的: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全球性的,我的節目也是問題之一。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更認識彼此,並且渴望了解我們祖先生長的地方。但在追尋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抗拒讓任何個人或單一聲音為整個社群代言的誘惑。」
就這點而言,他說得完全正確。